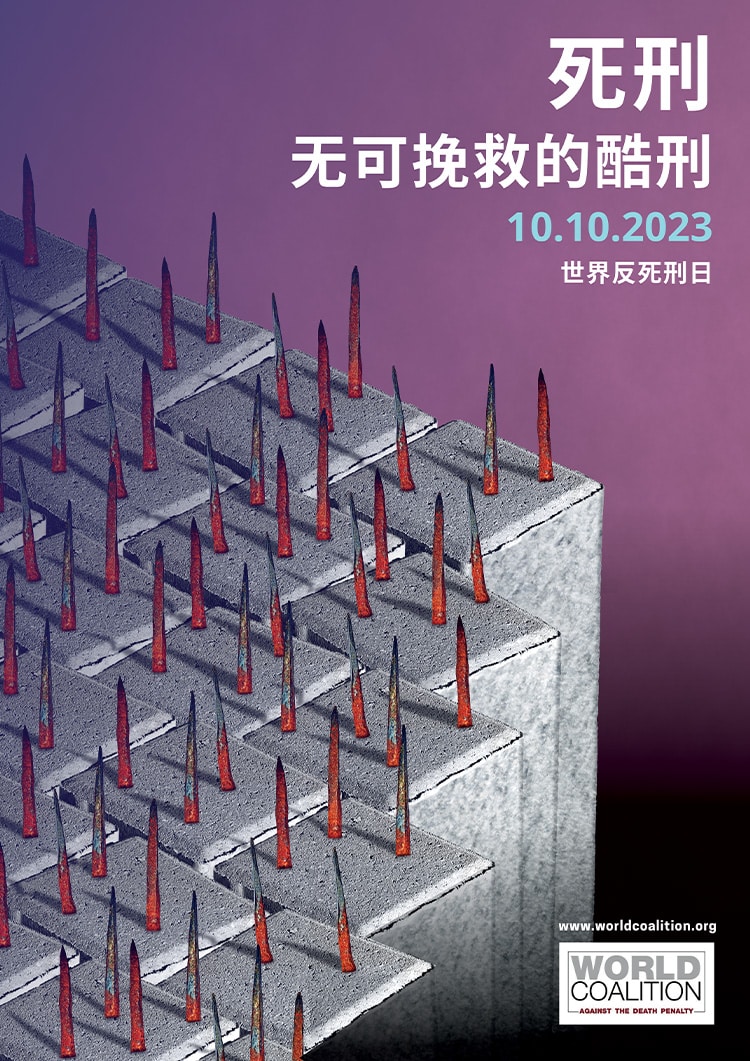【尊嚴.正義.生命權國際研討會】台灣死刑犯監所訪談計畫
亚洲
「尊嚴.正義.生命權」國際研討會將於9月21日(週四)舉行,邀請來自立陶宛、瑞士、英國、美國、印度以及台灣各界專家,討論台灣死刑犯訪談計畫、被害人權利保障法制發展以及死刑憲法訴訟的各國經驗,一同探討推動尊嚴、正義與生命權的下
一步。場次一:台灣死刑犯監所訪談計畫
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說,二十年前廢死聯盟剛成立的時候,就想要調查和重構死刑犯的人生樣貌,但當時根本不知道死刑犯在哪裡,國內也只有行政院研考會於1990年代調查發布的資料。直到2020年,廢死聯盟和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、法務部矯正署合作,研究才得以開啟。本計畫希望呈現死刑犯及作為對照組的無期徒刑受刑人的成長背景、在監生活和處遇;期待結果最終彙整成供政府參考的政策建議,讓未來長刑期收容人能獲得更恰當的處遇。
研究方法
林欣怡強調,這份研究不受政府委託和審查,且經費自籌,受訪者相對願意吐露真心話。受訪者包含三十七位死刑犯以及四十三位無期徒刑犯,對他們進行量化問卷和質性訪談,另設計機構問卷給監所管理人員填寫。研究團隊預先請已出監的死刑平反者過目,確認問題設計是有效、可被理解的。執行方式為,第一次與受訪者見面先進行知情同意,說明計畫內容與風險、確認意願,讓受訪者知道,訪談空間是獨立區隔的,監所方只能看、不能在旁監聽紀錄;訪問過程會全程錄音,以便檢視正確性及分析,資料將匿名保密並在最後銷毀。林欣怡說,有幾位死刑犯主動表示希望不要銷毀,因為這可能是他們在世上僅存的影音紀錄。
基礎資料分析:成為死刑犯以前
這份期中報告只呈現死刑犯的資料,待全部訪談結束、分析之後,才會公布更全面的內容。根據死刑犯的訪談數據顯示,三十七位當中有近三成是六十歲以上的長者,最高齡七十一歲。七成以上沒有高中畢業,超過半數是第一次入監,犯案時平均年紀是三十歲,平均關押時間約二十年。這些同學幼時普遍缺乏穩定親密的照顧者,父母長輩忙於工作;在家裡或學校遭遇體罰或霸凌,讓他們寧願早早出社會,但工作狀況又不穩定。有些人會在少年感化院、管訓隊或其他地方認識到混兄弟的朋友,「看到他們生活這麼好,很羨慕。」成長的種種條件讓他們不知不覺間成為走鋼索的人,稍有不慎就會跌落。心理彈性低、缺乏情感資源也是值得注意的面向;不少人因為爭執當下無法控制情緒,才會衝動犯下罪行。
2006年7月1日刑法修正,無期徒刑關押二十五年後才能申請假釋,在此之前是十五年。我們訪談的這三十七位死囚當中,有二十六位是在新法施行前犯案,若是判無期徒刑,他們現在幾乎都已經可以申請假釋了。此外,當年根本沒有情狀鑑定、量刑前社會調查或者兒童最佳利益等評估,也就是說,如果按照現在的司法品質來裁量,他們很可能不會被判到死刑;這也反映了死刑的恣意性。
監所的日常生活
台大社工系Ciwang Teyra教授接著談到,訪員團隊努力讓量化問卷提問的用字生活化,準備圖表化手卡,讓受訪者更明白一到五分的意義。同學們都談到飲食狀況很糟,有人甚至曾在菜裡吃過鐵絲。水質更是堪憂,洗澡水和飲用水常見汙濁,讓他們皮膚過敏、腹瀉。監所合作社可以購買基本生活用品,但供貨不穩定,會被任意取消訂單。受刑人高齡化和長照的問題也一直被忽視,他們牙齒和健康變差,飲食卻無法跟著調整;能買到的保健食品又很有限。
死刑犯住在兩坪不到的空間,遇到較友善的管理人員才能到走廊上活動。若要寫書法或畫佛像,只能跪在窄仄的房內。睡覺和洗澡的地方沒有隔間,平日固定時間需要儲水,舍房潮濕,幾乎人人都有濕疹。監所內的光線和噪音相當干擾睡眠。這些生活環境其實容易帶來疾病,但所方又不樂見戒護外醫,通常只給基本藥物壓制症狀,往往得等到半個月以上才能申請到外醫。
所方安排的心理諮商只有二十分鐘,難達效果。規定寫明,每天有一小時到戶外場地的放封時間,但實際上不是每個監所都做到。家屬接見次數雖然不受限,但一周只能見兩次朋友。Ciwang以人們住學校宿舍的情境來類比,死刑犯會和短刑期受刑人或羈押被告關在一起,所以他們要一直適應新室友;新入監的室友通常什麼都沒有,因此多少要給予協助,這對死刑犯而言都是負擔。死刑犯同學認為,若有獨居或專區的規劃,他們的狀態也會相對穩定。監所裡大大小小不合理的事情,表面上有陳情管道,其實申訴的機制不甚暢通,很難帶來實質改變。諸多規範都考驗和削弱著同學們的身心健康。
待死現象:以這樣的身分活著
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政策中心主任黃嵩立教授根據訪談逐字稿,把受訪者重複說到的內容抽取出來,做主題式分析。他說,死刑不只是一個抽象政策,還包含被判處死刑的人們每天的生活實況。多位死刑犯同學提及原封不動、毫無進展的時間感,就是過一天算一天。社會大眾常說,囚犯花納稅人的錢,吃免費牢飯;事實上他們在裡面的日常開銷大多需要靠親友接濟,因此讓同學們都有拖累家人的感覺。
Ciwang說,死刑犯不被允許跟其他收容人一起下工場,所以不像其他收容人有勞動和收入,許多同學想要自己賺點津貼,想學習一技之長,或者想彌補受害者家屬。但監所最多同意他們把勞作帶回舍房裡,一坪多空間還得擠滿用具;以監所內常見的作業項目之一摺紙蓮花來說,天天做,每個月頂多領一千多元勞作金,還會把窄小的舍房弄得髒污、擁擠,種種原因都降低死刑犯參與勞作的意願。黃嵩立呼應道,自立生活會帶來尊嚴,監所制度卻在剝奪他們勞動的機會,讓死刑犯失去社會角色的意義。「你要派我去看守核廢料也好,上戰場也好,讓我做事情,我覺得這才是人嘛。」不只一位同學有類似回饋。
面對執行
早年台灣的死刑定讞後,幾天內就會槍決,死刑執行快得讓人猝不及防。同學們說,現在面對長期等待的煎熬,沒有好到哪裡去。沒有尊嚴、不知道終點的等待,比死亡本身還痛苦。龐大的不確定和拖磨讓他們寧可趕快去死,也不要毫無希望地被關在那裡歹活,等於被糟蹋。他們甚至覺得自己的性命被當作政治工具,用來消弭社會不滿。幾位同學有宗教信仰,說不怕死,倒是很牽掛家人。漫長的囚禁裡,好些個人眼睜睜看過同舍的獄友,被拖出去執行。要如何陪伴即將赴死之人、自己要怎麼調適,這是另一個嚙咬他們神經的處境。
有些同學說,原本可以布置舍房,但換了新主管,就要求他們把心血通通拆光光。長期被關押者生活缺乏自主性,每天吃飽睡、睡飽吃、等死。待死現象以及附隨的缺乏自主性之感,是精神疾病容易找上門的關鍵,多位死刑犯同學有睡眠困難、憂鬱症、強迫症。曾經企圖自殺的人不在少數,之後被用精神科藥物控制,卻落入無法真實感覺自我的用藥狀態。
有意思的是,多位死刑犯表示支持死刑這個制度,但審判必須公正。多位同學感覺自己在司法程序當中沒有得到合理的對待,例如有利的證據未獲採信,其中還有含冤未雪的死刑犯。即使不是針對自己案件在表述意見,他們也看見其他死刑犯的境遇,覺得法官應該多考慮被告的背景,尤其是那些第一次犯案者。黃嵩立指出,很多人會對法官說:「你就判我死刑好了。」這份乾脆其實是一種對程序的抗議,因為他們在執法過程被誤解、不被尊重,想要趕快了結痛苦。現行的矯正機構環境和教化資源極度缺乏,也是棘手的問題;司法如何宣告一個人有無教化可能性,需要更多商榷和實證考察。
印度的死刑犯調查
Maitreyi Misra是印度「39A計畫」心理健康和刑事司法主任,她談到,印度目前有大約五百五十位死刑犯,光是2022年就有一百六十五個人被判死。本次她分享的資料來自2016年發布的印度死刑報告,該計畫是在2013-2015年間進行,訪問到三百七十三位死刑犯。這群人當中,有63%是家中唯一的收入來源,有六成左右未受過中學教育,多數來自社會底層;而且印度有種姓制度,呈顯了宗教和社會階層在死刑審判帶來的影響。Maitreyi說,計畫過程中,有些人後來改判無罪或者減刑,由此可見審判的任意性。
另一份研究從精神健康角度評析印度的死刑,可以看見,死刑犯很高比例擁有「童年逆境經驗」,某位死刑犯回憶童年目睹爸爸打斷媽媽的手,他如何漸漸有用藥和自殺傾向。印度死刑犯的群體之中62%有精神疾病,11%是智能障礙者。他們的心理狀態,無論是犯案前便有的,或是犯案後長期關押所致,都未被正視。
Maitreyi描繪印度死刑犯的待死現象,和受監禁的狀況。監所光線不足,生活環境同樣很差;縱然如此,有些死刑犯出身極窮,從小一天只能吃一頓飯,甚至會覺得在裡頭過得比較好,至少不會餓肚子。印度死刑犯一半以上有自殺意圖。某位囚犯自述,得知被判死之後,好像白色囚服就要往他身體裡咬去,把他咬死。另一位死刑犯原本在牢裡可以畫畫,這項活動取消之後,他就開始想死,想走進廚房拿熱油燒死自己。還有一位尋死的死刑犯,他被單獨監禁六年,除了不知道何時要被執行,他也擔心死後屍體會被丟出去被狗咬。
Maitreyi說,印度被判死的女性比例和數量,比台灣還要高。某位女性死刑犯入監前很活潑、愛打扮自己,但監所管理員說:「你的家人以為你已經死了,他們甚至沒有想要來看你。」讓她陷入很深的憂鬱。綜觀來看,印度死刑犯的心理健康問題同樣很嚴酷。林欣怡回應到,台灣法務部會為死刑犯安排心理諮商,但同學們不想被汙名對待,也不想被視為有問題的人;更重要的是,如果生活環境沒有改善,諮商師無法帶來什麼神奇變化。
英國的司法精神醫學
來自英國的Richard Latham作為司法精神醫學顧問,在英國的醫院和受刑人相處與工作。他說,從台灣、印度和英國的情形來看,如果一個人有心理和精神問題,較容易遭遇死刑。如果有精神問題,律師如何代表當事人呈現意見,這是個難題。因為精神問題是創傷的後果,這些犯案者要面對精神病汙名,此外他們往往無法和人建立實質關係、無法信賴他人,就會很難和律師有良好互動;這些人格障礙,導致他難以公正地使用司法。如果犯案者身心狀態差,表現出沒有悔改和不願道歉的態度,也會影響他是否被判死。
Richard坦言,精神醫學有其侷限。當精神科醫師斷定一個人無法教化,是認定他無法透過病理治療、可能是有危險的,但不代表他沒有其他療癒或變得更好的方式,因為這個人可能受過很複雜的創傷。而且精神科是透過病患的反應來診斷,不是仰賴他們真正的心理素質。好比,智能障礙者常常隱藏自己,想展現出有能力的一面。精神科專家無法每次都立即辨認出精神障礙者;所以如果持續有死刑,就可能有「未被認出來的」精神障礙者被判死刑。
觀眾提問時,Richard特別補充道,英國監所劃分成不同區域,有心理問題的受刑人會被區隔出來;監所管理人員可以有不同心態面對,不會妖魔化看待。此外,英國的司法醫院由國家衛生部門間接管理,全國司法醫院的醫療和保安人員共約有九萬名,大概有七千五百張病床。如果受刑人在監所狀況不好,就會到司法醫院。但經營司法醫院的成本是一般監所的兩倍,國家矯正系統必須開放協商,才可能有監獄以外的選擇。
研究死刑犯的意義
英國「死刑專案」執行長Saul Lehrfreund律師提到,他們在孟加拉和非洲肯亞做類似研究,和台灣、印度有很多共通的發現:死刑犯大都是弱勢、教育程度和收入低、有負面童年經驗或者有精神障礙。像這樣從客觀數據和資料著手,重構每個人的背景和經驗,我們可以清楚看到,死刑犯就是人,而死刑就是在剝奪人性和尊嚴。說出這些人的故事是重要的,因為關於死刑的論述都會拿掉人性。Saul提醒,這些研究正在打造新的論述,改變社會對話氛圍,拆除大眾刻板印象。
最後Saul分享,他曾聽過一位待死十四年的死刑犯這麼說:「每天起床睜開眼我就死了一次,日復一日。」判死不只包含執行死刑而已,比執行死刑這件事本身還要更糟糕,因為待死現象是更綿延而沉重的折磨。